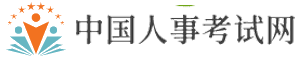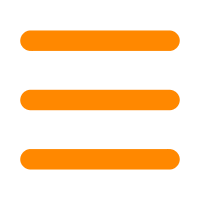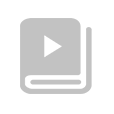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
走出危机第一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办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如果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离别。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少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
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因为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以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趋势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剖析,达成法的一般理论向西办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以外进步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觉得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1]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剖析是欠妥的,但,它却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剖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打造在规范剖析之上并为规范剖析服务。
国内的法理学状况怎么样?国内的法理学来源于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进步规律来讲,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办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的——找出法律进步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势必灭亡,苏联法是最早进的法打造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有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遭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国内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形解析。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的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改革开放将来,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舍弃,但政治哲学味道仍非常浓。近年来价值剖析和规范剖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但价值剖析和规范剖析一直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剖析探寻“规律”这一哲学的。
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达成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打造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怎么样打造人际合理关系的知识。当然,大家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非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括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含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不同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含法律的一同性的技术。
2.调整赞同识形态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要紧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来自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概念本身就是在1938年首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掌握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事实上没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不少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2]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环境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国内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导致的学术空间,并飞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环境中具备某种势必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后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比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用途、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非常不错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看法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很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它使法理学很难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便识形态之风摇摆;它使法理学很难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定义和基本观念一直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很难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比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不是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没办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其次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比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块,等等。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少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少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备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没办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没办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引导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离别是不现实的,但,这不可以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原因。预防法理学意识形态化应该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可以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比如不可以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办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应当引起足够的看重。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研究职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同他一个人的实质评价是不是认可不同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3]国内法学意识形态化的紧急后果之一就是将我们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紧急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需要的。
3.从“讲解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讲解性、评价性”法理学
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如果讲解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样,它应该在讲解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少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首要条件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离别,不然所谓成就就是纯主观的需要与欲望,缺少科学所需要的起码的客观性。假如大家的法理学具备这种评价能力,则国内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这样大的弯路,付出这样昂贵的学费。假如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遭到法理学的评价,假如公社化运动免费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遭到法理学的评价,假如“5·16”公告遭到法理学的评价,假如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遭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或许早已建成了。
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
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没有分歧,但在实质操作上却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剖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看法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目前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不过法律进步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看法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尤其是在如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比如大家马上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规范。同时,如今法律除去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剖析对象都着重于剖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只从本国法总结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由于其他人的经验都具备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没办法抽象出常见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大家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规范的描述,前者应当尽可能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量防止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规范描述的成分,不然,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规范学”了。
[1][2]下一页